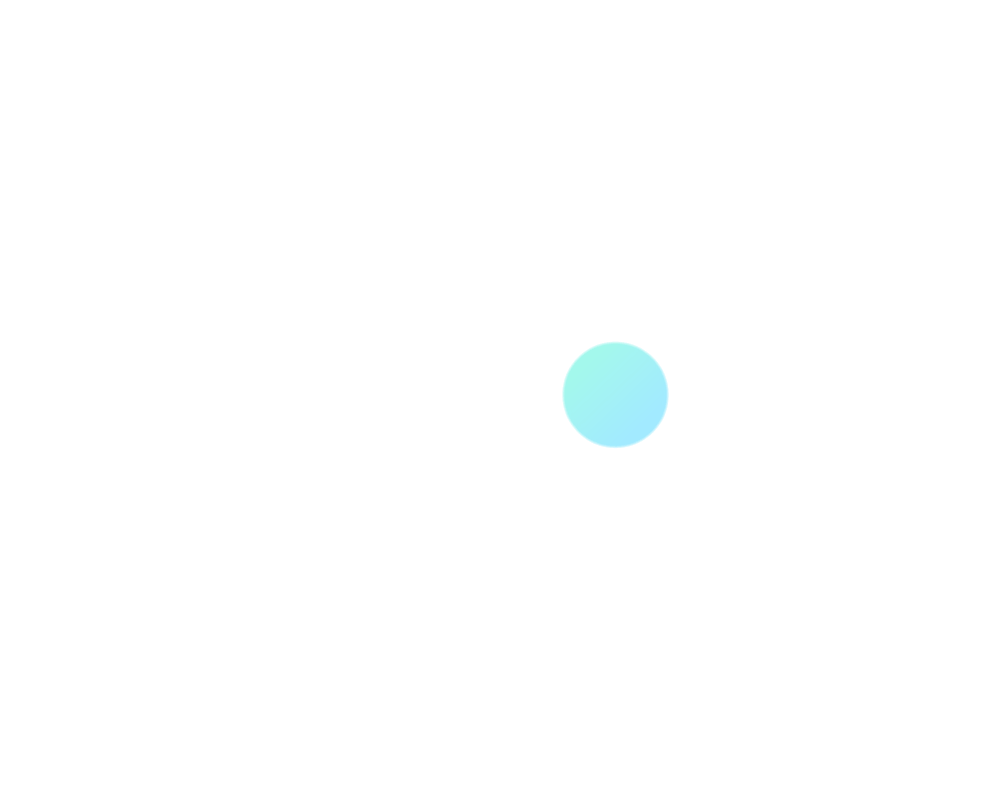关于时间的困惑
本文最后更新于 2025-10-22,最新编辑已超过90天,注意内容时效性。
工作之后常常会听到朋友在周末的晚上向我抱怨周末过的快,或者在难得假日的最后一天抱怨这个假期真快之类。“过的快”,我是认同的,但这时候我往往会在心里补一句“工作日也不慢”。
大概从中学时候起,我意识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,快到我们的一切感情都可以被它抹平,一切行为都在时间的尺度下变得无趣。以至于我们在看待时间这个毫无感情的物理量时,总会忍不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,就像是在时间压制下一切无趣的事物中,衬托得时间本身倒是有趣了些,可以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时间从来不知道有后退的选项,它就像一个检票员,严肃地守在闸机口,对每一个通过的事件盖下“历史”的印戳,而后再也不见。你若是想要让它流连,这位检票员只会平静而威严地催促着前进,低声几句后,你再不能反驳。
因此,我们在讲起过去的事情时,总会带着几分淡漠,哪怕是再深刻的事情,哪怕是死亡……这些淡漠似乎并不是我们主动带上的,但我们也无权拒绝。时间的声音是那样平静、无感却充满威严,不可抗拒。
上周末看到杨振宁先生离世的消息,我平静许久的内心又涌出一股难言的感情,像是遗憾、震惊又有些许的困惑,困惑持续到了今天。作为大时代下的普通人,我们时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消息感到心情的波动,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值得人们心情波动的事情很多,能让人们停下为之思考的东西却并不多。
我的困惑来源于我熟悉世界的标杆又倒下了一根。
从出生起,我们在父母、社会、学校的引导下建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,将一个个我们认定为价值的人事物作为我们世界认知的标杆,建立一个庞大的认知体系。而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又不得不面对儿时世界的崩解,新观念的重塑,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熟悉,又不得不越来越认真地去熟悉这个世界。
大学时候,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,原话我不记得了,意思大概是说:
人们很容易接受自己少年时期已有的事物,认为它们就是世界本身的样子,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
人们很乐意接受青壮年时期发明的事物,认为它们都是进步的、会改变世界的、革命性的。
人们反感自己年老时产生的一切事物,认为它们中的科技是会摧毁世界的、它们中的观念是大逆不道的。
这个说法很有意思,在漫漫时间长河之中,我们普普通通的一生何其短暂,却又何其冥顽不化。说简单一点,我想是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”,这个本性便是青少年时代形成的观念。时间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这一切,在极短的时间内固化一个人的认知,又用弹指一挥之力让人在毫无知晓中过完了自己顽固的一生。
当然,我们当中有一些充满智慧的人有能力突破时间的禁锢,在他们优秀的一生中都在与时俱进,时间无法固化他们的思想,杨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当然,也许有一天物理学家,数学家或是生物学家会得出一条结论,那就是一切淡漠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时间,而是我们人类早产的、脆弱的神经系统。让我们的记忆体系“对过去、当下和未来充满执念”又同时对过往的一切不再同情。
科普UP主毕导有一个关于对数的科普视频令我印象深刻,视频用对数揭示了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时间越来越快,并推导结论“人生的中点其实是18岁”。我以浅薄的数学知识深刻认同这一结论,并乐意以人生的厚度去理解它。数学原理不在这里讨论,只是令人对时间再多了几分敬畏。
回到最初的讨论,我们的感知也正是如此,对数的时间足以抹平我们的一切感情。人对一切充满了感情,最后却不得不在时间的面前平淡地面对一切。恐惧、困惑、遗憾都在一瞬间灰飞烟灭,而时间依然无所顾忌,毫不在意。
无月之夜,常有瞎想,没有逻辑,这种文字少有发出来的,但改了就不是本意了,凑合看吧。